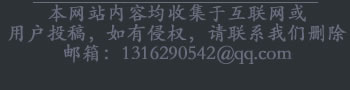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个身体:作为女人,以及作为君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0期,原文标题《女王的两个身体》,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茱莉娅·贝尔德在《维多利亚女王》中刻画了女王复杂的性格:情绪多变、感情外露、固执己见、意志坚强……
文/维舟

作家茱莉娅·贝尔德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自此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对当时的清廷官员们来说,这些“英夷”处处都不可思议,与历来所见的“夷人”都有所不同,而最可惊讶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居然是个20岁刚出头的少女。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是英国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全盛时期: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势力还基本仅限于本土,治下不过30万平方公里、500万人;乔治三世手里则丢掉了北美殖民地,美国自此独立;至于现任伊丽莎白二世,从1952年登基起,继承的就是一个后殖民浪潮下不断缩水的英帝国,而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却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统治着全世界可居住面积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一个人(且不说女人)达到过这样的巅峰。
正是在她统治期间,英国真正完成了自己的现代转型。当她1837年登基时,马车仍未被火车取代,英国还有多达近半数的人口不识字,工厂普遍使用童工,连伦敦都只有20%的儿童上过学,而到她1901年溘然长逝时,地铁、电报已普遍使用,受教育成了一项义务,而女性也有了一些基本权益。
当然,确切地说,这些功绩并不应该完全归于她的治理能力,因为根据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她所扮演的只是国家的象征。可能也是为了让这一象征显得更为完美,后人在编选其书信时,系统性地净化了她的言词用语,删掉了任何可能让她显得“过度强势、不够端庄或者言语不逊”,以及存在政治偏见的词语。然而,事实上,翻开这本维多利亚女王的秘密传记可以发现,在她身上交织着各种矛盾。

《维多利亚女王》
本来,对于像她这样的伟人而言,这种复合性也是事理之常,但在那个年代,作为世界头号帝国的女性统治者,可想会尤其不寻常。英国史学家约翰·希利在1883年曾说,大英帝国是“无意中”得来的,那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维多利亚女王也是无意中得到王位:虽然她一出生就是英国王位的第五顺位继承人,但小时候她最大的梦想仅是逃脱母亲令人窒息的掌控,在自己的房间里单独睡觉,以至于她成为女王后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将自己的床搬离母亲的卧室。少女时代的她常被人贬低为自私、愚蠢、自负甚至轻浮,也并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即位后也一度在国外被视为“悍妇女王”——她不是“生而为女王”的,而是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逐渐“成为女王”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她如何学习“扮演”并胜任女王这个“角色”?她漫长的一生见证并开启了欧洲君主制从直接权力转变为间接影响力的时代,这意味着实际统治逐渐转交给议会之后,象征性权力才成为对君主而言最为重要的存在。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一点上做得尤为成功,不仅因为英国君主立宪制天然更适应这样的时代大势,恐怕也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不那么有权力欲,而其甜蜜、简单的家庭生活却更能代表当时英国主流的中产生活。
女王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见。她和父母一样都是辉格党人,也始终希望由辉格党人来担任首相,甚至一度怒不可遏地说过“托利党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但正如这部传记所洞察的,她也常常被个人性情左右自己的判断:她早年深深偏爱的墨尔本勋爵表面上是辉格党人,但其实本质上是个保守派,而她晚年时最喜欢的首相迪斯雷利甚至成功地将她转变为保守主义事业的支持者。这些都意味着,她真正看重的与其说是某种政治信条,倒不如说是某种上层社会的格调:墨尔本勋爵的风趣、迪斯雷利的奉承才是她真正乐在其中的,而托利党人罗伯特·皮尔的冷漠腼腆、自由党人格莱斯顿的刻板孤傲,都是她避而远之的。迪斯雷利曾一语道破:“格莱斯顿把女王当作一个公共部门来对待;我把她当作一个女人。”
16世纪英国法学家曾创制“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概念,意指国王既有一个“自然之体”(生老病死的肉体),又有一个“政治之体”(可存续、不可朽坏的国家象征与权力地位),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里有“女王的两个身体”:作为女人,以及作为君主。在维多利亚女王身上,我们恰好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冲突:有时即便在履行君主职责时,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人偏好都不免涉入进来;但另一些时候,她似乎又只想做一个女人,把自己身为君主的职权让渡给自己的夫君。
这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女王一次晚归,敲门时,她的王夫阿尔伯特在里面问是谁,她答:“是我,女王。”门没有开。过了一会儿,她才低声说:“我是维多利亚,你的妻子。”此时门才打开了。这常被视为一个温情的家庭故事,但不如说很好地体现了女王的双重角色。按说她应当独自统治英国,但她生养了多达九个子女(随着后代在各国王室开枝散叶,她晚年时因而成了“欧洲祖母”),即便不会容忍他人攘夺自己的权力,但至迟到结婚五年后的1845年,阿尔伯特就成了真正发挥君主职能的人。一如本书所言,“阿尔伯特的勤奋、节俭、拘谨、虔诚以及想要驾驭19世纪时髦活动的渴望,从许多方面说比维多利亚本人更好地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
虽然生了那么多孩子,但女王却很难说是一个好母亲,她对母乳喂养有着“完全无法克服的厌恶感”,并曾毫无顾忌地对自己女儿说,生孩子“对于一个人的一切得体感都是一种彻底的侵犯(上帝知道,光是结婚就已经对得体感造成了足够的冲击)”。在这里可以看出,她对上流社会格调的认同压倒了自己身为女人的角色认同,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以她名字命名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是一个强调女性节操和母职的保守时代,甚至后世想起时的第一印象就是“假正经”。
她支持女性“得到合乎情理的教育”,并且五个女儿中的四个都成了女性权益的倡议者,但在她看来,伸张女权是“疯狂”之举,“忘了一切淑女的感受和礼仪”。她和格莱斯顿唯一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件事,就是给予女性投票权或任何政治权利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与之同时,她却又不断给这位首相施压,要求他屈服。在这方面,最能显著地体现出女王所扮演的是自己的君主角色,而非一个女人。
最终,这印证了当时英国政治体制的制衡与弹性:女王也许很难大公无私,也可以有自己的个人偏好,但却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左右政局(发动鸦片战争的巴麦尊勋爵,一直是她非常厌恶的危险人物,但他仍能无视她的存在);她的很多价值观都体现出上流社会的特质,对普通民众(更不必说对更为边缘的女性)有距离感,以至于虽然在私人生活中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但在公共事务中却不由自主地更多是在扮演“君主”的角色。正是立宪君主制预先防范了她个人意志带来权力越界,让她不得不见机行事地妥协,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国家象征的角色。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种对权力的限制,最终反而使英国的君主制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影响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那么多王冠落地之后,它却能长盛不衰,延续至今。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再测珠峰》,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